| [1] |
LIM G, GOMEZ E T, WONG C Y. Evolving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an introduct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21, 51(5): 697-712. doi: 10.1080/00472336.2021.1934720
|
| [2] |
KANCHOOCHAT V, AIYARA T, NGAMARUNCHOT B. Sick tiger: social conflict,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and exclusive growth in Thailand[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21, 51(5): 737-758. doi: 10.1080/00472336.2020.1869997
|
| [3] |
EVANS P B.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4] |
周黎安. 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J]. 社会, 2021(6): 1-40. doi: 10.15992/j.cnki.31-1123/c.2021.06.001
|
| [5] |
黄冬娅. 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J]. 社会学研究, 2013(5): 172-196. doi: 10.19934/j.cnki.shxyj.2013.05.008
|
| [6] |
耿曙, 刘红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演变[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18-2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DZS201806004.htm
|
| [7] |
张国清, 马丽, 黄芳. 习近平"亲清论"与建构新型政商关系[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5): 5-1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XB201605002.htm
|
| [8] |
黄冬娅.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J]. 社会, 2014(4): 138-16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EH201404007.htm
|
| [9] |
周黎安.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 社会, 2018(2): 1-4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EH201802001.htm
|
| [10] |
张向东. 从依赖到协同: 农村政商关系的历史演变[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3): 85-8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XGL201803020.htm
|
| [11] |
冯伟. "筑巢"与"引凤": 政商关系对FDI的作用特征与机制分析[J]. 财贸研究, 2021(7): 27-4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MYJ202107004.htm
|
| [12] |
孙德超, 钟莉莉. 基于"亲"和"清"不同组合的政商关系的类型划分及转化机理[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7): 160-16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JLW201907020.htm
|
| [13] |
杨典.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11): 30-35. doi: 10.14063/j.cnki.1008-9314.2017.02.007
|
| [14] |
符平, 李敏. 基层政商关系模式及其演变: 一个理论框架[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1): 194-20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DSK202001022.htm
|
| [15] |
GUNTER F R. Corruption, costs, and family: Chinese capital flight, 1984-2014[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43): 105-117.
|
| [16] |
方明月, 聂辉华. 腐败对企业契约实施的影响: 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5(4): 119-12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SH201504015.htm
|
| [17] |
NGUYEN T T, VAN DIJK M A. Corruption, growth, and governance: private vs. state-owned firms in Vietnam[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2, 36(11): 2935-2948.
|
| [18] |
MURPHY K M, SHLEIFER A, VISHNY R W.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2): 409-414.
|
| [19] |
夏后学, 谭清美, 白俊红.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9(4): 84-9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YJ201904007.htm
|
| [20] |
黄少平, 蒋政. 借反腐大势重构廉洁官商文化[J]. 宁夏社会科学, 2016(1): 32-3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XSK201601006.htm
|
| [21] |
韩喜平, 孙小杰. 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分析[J]. 理论学刊, 2017(5): 18-2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LSJ201705003.htm
|
| [22] |
汪锋, 姚树洁, 曲光俊. 反腐促进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理论机制[J]. 经济研究, 2018(1): 65-8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YJ201801006.htm
|
| [23] |
邓慧慧, 刘宇佳. 反腐败影响了地区营商环境吗?——基于十八大以来反腐行动的经验证据[J]. 经济科学, 2021(4): 84-9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KX202104007.htm
|
| [24] |
倪星, 王锐. 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 一种理论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5): 116-13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SHK201805006.htm
|
| [25] |
王帅. 法治、善治与规制——亲清政商关系的三个面向[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8): 99-10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XGL201908021.htm
|
| [26] |
黄毅. 市场化进程中政商关系的共生庇护、寻利型变通与治理之道[J]. 地方治理研究, 2021(4): 16-3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XXZ202104002.htm
|
| [27] |
梅德平, 洪霞. 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J]. 江汉论坛, 2018(8): 31-3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HLT201808005.htm
|
| [28] |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城, 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65.
|
| [29] |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共识与冲突[M]. 张华青, 林恒增, 孙哲,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
|
| [30] |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 [31] |
HURWICZ L. The design of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2(2): 1-27.
|
| [32] |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 余逊达, 陈旭东,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54.
|
| [33] |
高庆鹏, 胡拥军. 集体行动逻辑、乡土社会嵌入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3(1): 6-1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WS201301003.htm
|
| [34] |
BATES R H. Contra contractarianism: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J]. Politics & Society, 1988, 16(3): 387-401.
|
| [35] |
AOKI M. 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
| [36] |
梁平汉, 孟涓涓. 人际关系、间接互惠与信任: 一个实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13(12): 90-11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JJJ201402008.htm
|
| [37] |
胡洪彬. 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政治系统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21(3): 42-5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POLI202103004.htm
|
| [38] |
SEARLE J R. What is an institution?[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05, 1(1): 1-22. http://econpapers.repec.org/article/nosvoprec/2007-08-1.htm
|
| [39] |
黄冬娅, 刘万群. 被挤压的市场机会——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结构性困境与消解[J]. 探索与争鸣, 2022(9): 136-14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TSZM202209011.htm
|
| [40] |
马宝成. 政治权力制约监督的理论基础与运作机制[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5(S1): 100-102.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JXZ2005S1036.htm
|
| [41] |
颜德如, 岳强. 中国府际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向[J]. 学习与探索, 2012(4): 39-4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XTS201204010.htm
|
| [42] |
林尚立. 重构府际关系与国家治理[J]. 探索与争鸣, 2011(1): 34-3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TSZM201101013.htm
|
| [43] |
CHOI E K, ZHOU K X. Entrepreneurs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rent-seeking[J]. China Review, 2001, 1(1): 111-135.
|
| [44] |
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People's opium?[J].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 2003, 50(1): 225-282.
|
| [45] |
曹伟, 杨德明, 赵璨, 等. 地方政治权力转移与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周期——基于政企关系重构的动态研究[J]. 财经研究, 2017(1): 4-1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CJYJ201701002.htm
|
| [46] |
徐晋, 贾馥华, 张祥建. 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企业价值与社会效率[J]. 人文杂志, 2011(4): 66-8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RWZZ201104011.htm
|
| [47] |
靳文辉. 公共规制实施中利益机制的规范建构[J]. 法商研究, 2022(4): 3-17.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SYJ202204001.htm
|
| [48] |
ROUSSEAU D M, SITKIN S B, BURT R S, et al. 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a cross-discipline view of trus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3): 393-404.
|
| [49] |
MANSKI C F. 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14(3): 115-136.
|
| [50] |
郭士祺, 梁平汉. 社会互动、信息渠道与家庭股市参与——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4(S1): 116-13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YJ2014S1010.htm
|
| [51] |
郭鹏, 林祥枝, 黄艺, 等. 共享单车: 互联网技术与公共服务中的协同治理[J]. 公共管理学报, 2017(3): 1-1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GGL201703001.htm
|
| [52] |
姚远, 任羽中. "激活"与"吸纳"的互动——走向协商民主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141-14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DZK201302015.htm
|
| [53] |
GALBREATH J. How do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nefit firms? evidence from Australia[J].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2010, 22(4): 411-431.
|
| [54] |
AGUILERA R V, RUPP D E, WILLIAMS C A, et al. Putting the S back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multileve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n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3): 836-863.
|
| [55] |
孙明, 吕鹏. 政治吸纳与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改革信心: 基于中介效应和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9(4): 92-10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JSH201904011.ht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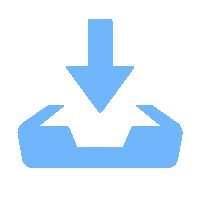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